





提起东汉张衡(公元78—139年),很多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,往往是地动仪、浑天仪,但若仅以科学家定位张衡,未免失之偏颇。实际上,他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,其赋、诗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尤其是他笔下的山水意象,既承继两汉大赋的铺陈传统,又渗透了个人的胸怀与哲思。可以说,张衡的江山描绘,不只是山川地理的摹写,更是科学眼光与文人情怀交织的艺术结晶。
以科学眼光观照山河
与同时代文学家相比,张衡的特别之处,在于他是一位天文家。天文视野,让他看山水时,总能纳入更辽阔的宇宙坐标。

在《西京赋》中,张衡描写都城长安周遭的山川地势:
“嵩高岱宗,降望伊阙。终南奄忽,横亘千里。”
这是典型的赋体铺陈,但他的描写并非单纯写“风景优美”。张衡以整体地理格局来观照山川,把山河视为天地秩序的组成部分,使得山水不再只是点缀,而是宇宙宏观结构的一部分。由此可见,他眼中的山水带有“科学之眼”:熟知方位与地理格局,将人文与自然相融,使山川既是景物描写,又是对天地之理的印证。
《南都赋》中的山川盛景
与《西京赋》侧重写洛阳帝都的壮丽不同,《南都赋》是张衡对故乡南阳的歌咏。张衡自幼成长于南阳,他熟悉这里的山川景致,因此在赋中所写,情感真挚而细腻。

他在赋中写道:
“其土膏腴,其水渟渟。山出美玉,川产灵龟。”
这里描绘的是南阳山川的丰饶:山川孕育美玉良材,江河出产奇珍异宝。
张衡用“膏腴”“美玉”这样的词,凸显自然的厚赐,既是山水之美的写照,也是对家乡繁荣的赞叹。 张衡在《南都赋》中,既铺陈山川之势,又细写田园之乐。与《西京赋》的帝都气象相比,《南都赋》中的山水更具亲切感,更贴近生活。他所描绘的江山,不只是政治中心的象征,更是乡土情感的寄托。
山水作为精神寄托
张衡一生仕途多舛,历经沉浮。他在京师洛阳多年,却常有怀才不遇之感,于是常常寄情于山水。

在《归田赋》中,他写道:
“于是乎弭节南亩,解带桑间。拥篲而耘,荷锄而耒。”
这几句并未刻意描绘山川奇景,而是通过农事的细节,勾勒出田园生活的闲适与自然。对于张衡而言,山水并非远在天边的风光,而是回归日常的依托,是他心灵的归宿。山水意象在这里,与“归田”的主题紧密相连,既是一种现实逃避,也是精神自守。
这种写法,正好与《西京赋》里恢宏的都城山川描写形成鲜明对比:在洛阳,山川是帝王气象的衬托;在田园,山水则成为心灵的宁静港湾。张衡的山水,因境遇而变,因心境而活。
山水中的家国与哲思
张衡在《西京赋》中,山水是帝业与礼制的象征;在《南都赋》中,山水则化为家国与乡土的承载。

一方面,他借山川丰饶,暗示南阳具备建都的条件;另一方面,他又通过田园之景,表现对故乡的热爱与依恋。可以说,《南都赋》中的山水,是张衡生命经验最直接的投射。
例如: “其地也,沃野千里,膏腴万顷。”
这既是对自然山川的颂扬,也寄寓了他对政治理想的映射:希望天下如南阳山川一般丰饶安乐。张衡的山水描写,始终有“以景寓志”的传统。

从“帝都之山川”到“故乡之山川”,再到“心灵之山川”,张衡的山水意象层层递进,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。
张衡笔下的山水,不仅是自然景物的描摹,更是政治理想、乡土情感与人生哲思的综合体。《西京赋》写帝都之雄伟,《南都赋》写故乡之丰饶,《归田赋》写田园之宁静,这三重山水,共同构成了张衡文学中的“江山三境”。
张衡的山水,正如他本人,既能仰观宇宙的浩瀚星辰,又能低首倾心于江山草木。
来源:南阳市博物院张衡博物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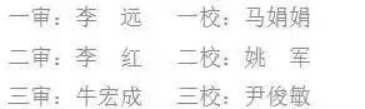



地址:南阳市鼎盛大道369号(光武大桥南段向南980米路西)

官方网站

博物院微信号

知府衙门微信号

张衡博物馆微信号